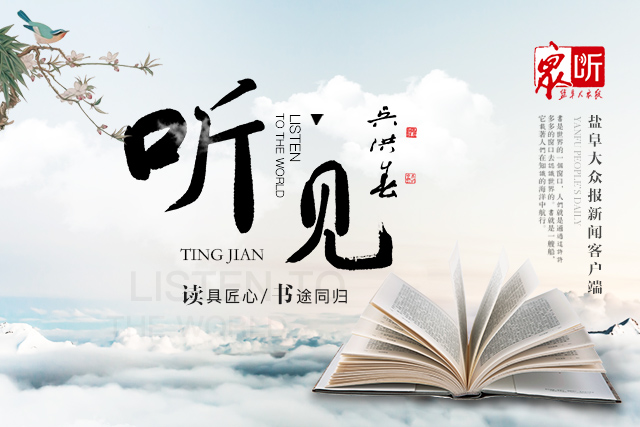
碧波重荡
●王其益/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总有一条河流,在城市血脉中静静低语。于盐城而言,串场河便是这样一条融汇历史与生命的母亲河。自唐代漕运的桨声中诞生,在盐晶光影间蜿蜒,将千载咸风与人间烟火,都揉碎于粼粼波光之中。而今我独立石栏,看夕照被水纹捻作金箔,竟恍惚难辨——是河水在流动,还是时光在回溯。
记忆里的串场河,曾是一轴声色交织的长卷。帆樯如林,船歌相闻,载满盐包的舟船于碧波间犁开雪浪。水是活的,呼吸间氤氲着湿润的朝气。而后陆上交通日盛,河床渐寂。废弃船只成了水上人家:窗隙漏出暖黄灯火,船篷升起炊烟,货舱改为商铺,甲板上彩衣如旗。初时确有“串场人家”之诗意,灯影倒坠,恍若银河碎落,可谁见河流暗吞苦楚?
河水最先发出叹息。碧玉渐成墨渍,清冽转作浊腥。微风送来的不再是水草清香。行人掩鼻,孩童不敢嬉水,河流成了城市一道溃烂的创口。
转机始于痛定思痛的觉醒。政府的告示沿河张贴,老船民抚着船头反复摩挲,眼中浮起疑惑的泪光。拆船之月,起重机长臂轻舒,将世代水居的旧梦温柔搁岸。有老妪抚舷不忍离去,直至小孙女指向新居欢呼“阳台能种花呢”,才颤巍巍踏出上岸的第一步。万条船舶解体迁离,清淤船轰鸣着掘出沉积的痼疾。河床在阵痛中裸露出千年记忆—一唐砖明瓷在阳光下短暂苏醒,又悄然沉入新时代的救赎。
治理河流,实则是修复与自然的契约。沿岸所栽,是对生态的敬畏;步道铺砌青石板,更是人与水重逢的盟誓。河水渐澄,先怯生生映出一角蓝天,继而坦然拥抱云影飞鸟。某日清晨,忽见垂钓者身影再度倒映水中,如蜻蜓轻点,漾开一圈圈等待多年的年轮。
今日之串场河,宛若盐城腰际的碧玉绶带。三十里生态公园如翡翠璎珞,四季流转:春樱拂雪,夏荷摇风,秋芦涌浪,冬梅映波。老人水边太极起落,衣袂飘拂间恍与唐代漕工号子同频;孩童追逐白鹭,笑声落水溅成晶莹音符;恋人月下携手走过亲水平台,誓言被流水吟成永恒诗行。
尤爱雨中之河。细密雨针将河面绣作轻绡,两岸楼台倒影被涟漪揉皱,晕成水墨长卷。恍见唐时盐船破雾而来,非为劳役之苦,而是穿越时空灵思,与今朝游舟相视一笑,共证一条河流的生死轮回。
夜色浸染时,两岸灯带渐次点亮。不复昔日零乱星火,而是匠心勾勒的光之长廊。金银光辉泻入水中,与星河交融难辨。画舫悠然驶过,船头琵琶声碎,奏出的已是现代城市的生态咏叹。这条千年运河之重生,实为人类对文明的二次叩问。我们曾截清流以逐发展,终又唤碧波而证觉悟。
串场之变,乃一部水的史诗,书写牺牲与救赎、遗忘与铭记、索取与归还。她以澄明昭示:真繁华并非征服自然之喧嚣,而是与万物共生的宁静。
伫立桥头,但见水天同碧,游云入河行走,飞乌溯光翩跹。串场河依旧日奔流,载着唐诗宋“盐”、明清帆影,更载着今人馈赠后世的碧波之梦。水纹荡漾之间,不惟云影天光,更是一座城市将生态伦理写入血脉的永恒誓言。
编辑:梁鹤龄 崔治国 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