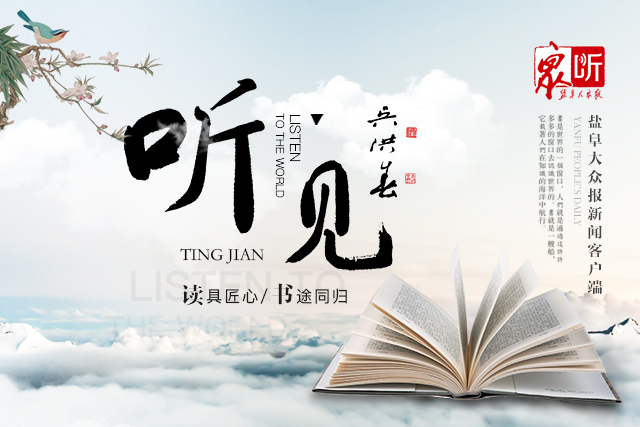
“唧唧”复“唧唧”
●王美东/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写道,“蟋蟀是蛐蛐的官名,它单独时名为叫,在雌雄相对,低声吟唱的时候则云弹琴……”“叫声”和“琴声”,其实是雄性蟋蟀通过翅膀摩擦产生的。
别小看小小的蟋蟀,它们可是非常古老的昆虫,已经在地球上生存和弹唱了上亿年,可谓子孙生生不息、技艺传承不怠。《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记录了夏历(后称农历)七月到十月蟋蟀们的迁移行踪。立秋前后,蝉鸣声渐渐式微,蟋蟀们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不知是哪只蟋蟀最先怯生生地搓弄翅膀,唱响秋天蟋蟀大联欢的序曲。这一声,唤醒天下雄性蟋蟀基因深处的音乐家天赋。于是乎,海滨内陆,天南地北,蟋蟀们开始齐奏起来。起初生疏拘谨,渐渐酣畅淋漓,“唧唧唧、唧唧唧……”唧唧声像细细绵绵的风卷过大地、卷过秋天。
家在平原。蟋蟀就潜伏在庄稼地里、草丛中,抑或藏身门前的碎砖间、花盆旁,甚至登堂入室,躲匿在堂屋的旮旯处、厨房的水缸下、卧室的床底柜底。小时候,常纳闷什么虫子在家中不辞辛劳地日夜鸣叫。辨明发声方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蟋蟀们仿佛已经猜透我的心思。还未走近,五六米开外,它们就陡然噤声不语。大步向前,急速搬开遮挡物,一个小小的身影似乎敏捷跳开,倏忽不见。有时左边叫声刚停,右侧又发新声,后方也开始絮絮叨叨,耳朵被迷乱了,根本找不准它们的藏身地点。
年少时,深秋的夜晚是一片海。躺在木床上,就像躺在一叶扁舟上,随波逐流,心思淡泊。白天的噪声,压住了音乐家们的琴声。夜晚的宁静,让它们成为声响的主角,成为夜晚的主人。这一只在厨房弹唱,另一只在过道试声,还有一只在窗台下呜叫…
你方唱罢我登台,低吟浅唱,夜夜欢歌,重复着它们简单又古老的田园歌谣。夜宿邻省小山村。山影簇簇,树影幢幢,陌生感和压迫感不断袭来,不能入寐。辗转间,山风似潮汐退去,蟋蟀们的叫声明晰起来。远近和呜,连绵不绝,“唧唧”复“唧唧”这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恰似他乡闻乡音。唧声如阵,心却静了下来。
今秋凉风姗姗来迟,夜晚终于可以关闭空调、推开窗了:“唧唧唧、唧唧唧”,突然久违的琴声穿过黑幕、穿过窗纱,传进耳朵里。
这自然的声响,遥远又亲近,琐碎又悦耳。年少时的场景历历在目,恍若就发生在昨天。如今人到中年,世事羁绊,很少留意这孜孜不倦的琴声和执着的“抚琴人”了。
如今无论身居何方,身处何时,一旦听到这“唧唧”复“唧唧”的琴声,就会想起诗行词阕里的蟋蟀声、 就会勾起内心深处绵绵不尽的亲情乡情。
编辑:梁鹤龄 崔治国 严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