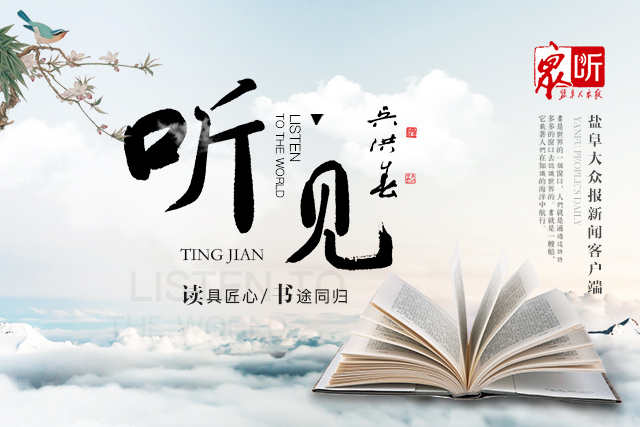
师者大舅爹
● 陈寅阳 /文
● 凌敏 /诵读/音频制作
吃晚饭时,岳母说,明天大舅爹从“海里”上来了。大舅爹是她的大哥。芸芸众生,舅爹为尊,何况行“大”。所谓“海里”,指靠海边的地方。老人们喜欢称更东的射阳为“海里”。
一个阜宁人,如何会不远百里去了“海里”?那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舅爹读了阜宁师范,毕业后被分配至邻县的射阳,做了乡村教师。然后就在“海里”成家、育女、生儿。渐渐他乡成了故乡,家乡反倒成了他乡。
师范毕业的大舅爹,辗转于射阳不同的乡村任教,办学条件也与时俱进,从土坯校舍,到砖砌教室,再到后来的楼房校园。从普通教师,到村小校长,职业生涯的顶峰是做了中心校校长。我虽未亲身经历大舅爹的前半生,但作为和他拥有同一母校的学生,我可以从三十年后自己在乡村任教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来想象还原他的乡村教师生活。乡村教师大舅爹,自有一股威严气。做了校长后更是不苟言笑,言语不多,不但晚辈,就连和他平辈的岳母等人,也都有些“惧怕”—一许是职业身份自然形成的气场。妻曾跟着他读过两年书,彼时他已是中心校校长。那时的农村学校,都会在校园一角或最后面,砌几间平房,作为教职工宿舍和食堂。校长和老师们以校为家,周边的空地亦不浪费,被老师们开辟成菜园,长些瓜、豆、茄和其他蔬菜,以供日常所需。每日早上,大舅爹先沿着校园的角角落落走一圈,然后走到妻的宿舍,查看她的学习。妻往往大气都不敢出。在大舅爹的严格督促下,妻终于考上了中专,跳出了农门。可以说,没有大舅爹的帮助,便没有妻的今天。妻总是心存感激,这份感激藏在心里,常用“大恩不言谢”安慰自己。
我与妻相识时,大舅爹正值盛年,又担任校长,是我这样的农村青年教师仰视的对象。我与大舅爹第一次见面是在乡宴上,妻的外公——大舅爹的父亲生日宴。我这个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不免战战兢兢、慌慌张张。开席前,我与大舅爹有过短暂的交流。大舅爹仔细地“面试”了我一番。依稀记得,“考题”挺难,内容是关于农村习俗和古代文化传统的,似乎还涉及某个字的读音、某个词的意思。其险若此!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大舅爹,承袭了这一群体的优良传统:严肃方正、遵循礼数、敬业负重。这一代师范生,大多默默无闻,一生清贫,没有惊天动地的功业,只是尽好为人师者的本分:授业、传道、解惑,陪伴孩子成长。但正是他们撑起了农村教育的天空,将一个又一个农家子弟培养成才,甚至有的家庭一家几代都是他们的学生。被定义为乡村教师,或者令名不彰,或许才华不展,但他们普遍受到乡人的尊重。
渐入老境的大舅爹,逐渐褪去了威严,变得越来越慈祥,甚至可爱。虽然脚步慢了些,但腰板依然挺直;酒不能多喝了,但喝酒的礼数一点也不少;听力也在减退,但似乎是选择性耳聋—一喜欢的听见,其他的不听也罢。时间是最好的黏合剂,本来素不相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成了亲人。
编辑:梁鹤龄 胡丽丽 王艺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