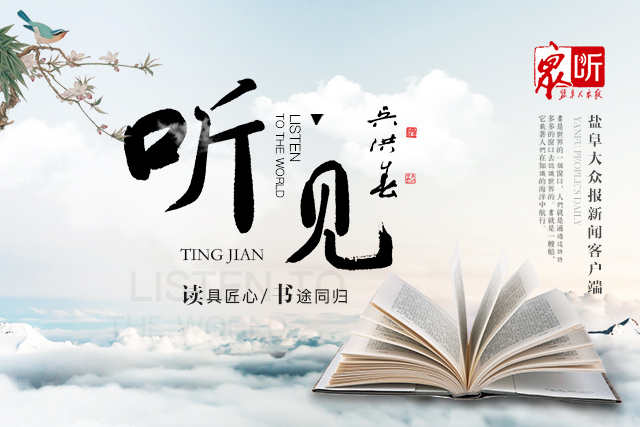
场上晒着陈玉米
●居著培/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来雨了!”午睡的我被一阵惊呼喊醒。睁眼一看,阳光照耀下,密集的雨丝像无数条金线扯天入地,直泻下来。
“不好!”我一跃而起,套上拖鞋,打开门,就往西邻飞奔。
西邻门前的水泥场上,大林和小莲两口子正手脚不停地忙着。大林用一把木锨把玉米往一起堆,小莲正抖开一张大油布。我甩掉两只拖鞋,冲过去,帮小莲扯住油布的另外两端,朝玉米上盖。
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遮住双眼,顺着脸颊脖子灌进汗衫。双脚被玉米粒硌得生疼。
大林也过来,几个人齐心把玉米盖上。
当我们把一切都弄好,站到走廊上,才顾着互相看看,都笑了。个个都成了“落汤鸡”!
再看西边几家门口,也是同样景象。根小夫妇,平小夫妇,都在忙着做同样的事。
他们晒的不是自家的玉米,是大成的。土地流转,大成响应号召,包了七八十亩土地。一年两熟,夏秋种玉米,冬春种小麦。他没有晒谷场,所以粮食都是晒在邻居家门口,顺带雇佣他们帮翻晒。每人每天80元。所以,抢场对他们来讲是义务,对我来讲是做好事。大成在自家场上忙乎,顾不上跟大家说一句感谢的话。他是个六十多岁的汉子,精瘦,皮肤黝黑。胳膊腿都像被炭烤过一样,泛着黑金属一样的光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闪着狡黠与精明。
“除去租金和农药等成本,两熟能收一熟的钱。好年成能收到八九百一亩,差年成就说不上了。”大林告诉我。
“今年,玉米扬花恰逢高温天,好多玉米都扬花不充分。收成肯定有影响。”小莲说,“我们昨天去帮大成撒化肥,看到不少玉米棒都有大片瘌子。”
她又给我看手腕处的累累伤痕。“看!在玉米地里干活,叶子像刀剑一样。玉米秆比人都高,人走动时,那叶子划人的脸,汗流过那些伤口,生疼。”“今年的玉米还在地里?那,这些玉米是哪儿的?
去年的?”我好奇地问。“是去年的。”小莲答。怪不得,我早上看到这些玉米是大春用电瓶车从大成建在河边的仓库里拉过来的。
“去年,玉米收上来,贩子来收,一块四一斤。有人卖了。后来,价格一天天降。单价一块二毛五的时候,我们也卖了。”大林说道,“大成不服气,继续等。等着等着,那一季的收购就过去了。”
“现在收购价是多少?”我问。“一块一毛五。”大林说。粮食存在仓库里,肯定只会越来越少。受潮、虫蛀、鼠害各种不确定因素。大成因此等待,错过了一次次出手的机会。可到最后,玉米也没有涨价。
这一放,放了近一年。这次不能不卖了。因为,新玉米快上来了,需要腾地方了。可见,市场是他们没有办法左右的,把握时机也很重要啊!
正说着话,雨停了,阳光又火辣辣的了。本来,夏天的这种太阳雨总是转瞬即逝的。于是,我又协助小莲打开油布,大林拿起木锨,刷刷刷,把玉米摊开。黄灿灿的玉米又铺开来,像一地金子。
编辑:梁鹤龄 胡丽丽 胥文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