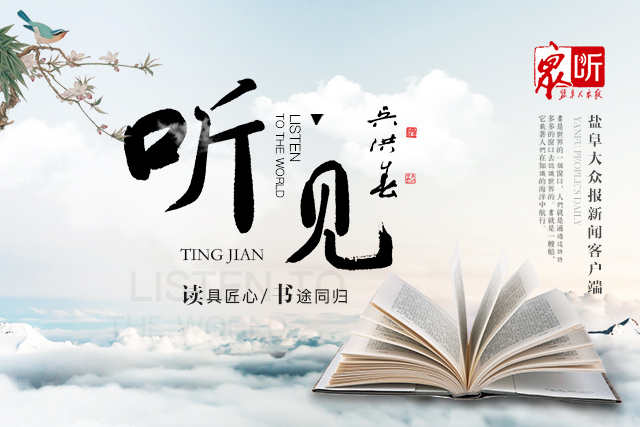
生活的模样
●子安/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公交车车窗上,凝着薄薄一层水汽。外面的人影匆匆闪过,模糊一片。车子轰隆隆地跑着,我的目光,却忽然被窗外“钉”住了。
路边那个小小的街心公园里,一位老人支着画架。他正对着几棵绿树,一笔一笔,画得极认真。暮色悄悄爬上来,染红了他的颜料盒。画布上的绿,鲜亮得像是刚从叶尖上摘下来的,还挂着露水似的。他就那么站着,画笔成了他丈量日子的尺子。
一样的黄昏,隔着一层车窗玻璃,竟像是两个世界。这光景猛地戳了我一下:生活啊,原不过是一团湿乎乎的泥巴,最后捏成什么形状,全看我们的眼睛往哪儿瞧,脚丫子又往哪儿踩。
眼睛落在哪里,哪里就亮堂起来。菜市场鱼摊的老板娘,手起刀落,又快又准。李老师爱吃鱼头,王伯家的小孙子馋鱼泡,她都记着呢。“张姨,今儿的鲫鱼活蹦乱跳,给您挑条顶肥的!”她眼睛弯弯的,声音也润润的。说来也怪,那油腻腻的砧板,那案板上蹦跳的鱼鳞,被她那双带笑的眼睛一照,竟也出几分光鲜来,腥气里仿佛掺进了一丝海风的味道。原来,目光落到的地方,再平淡的日子,也能像上了釉的陶罐子,温润地泛着光。脚往哪儿迈,路就在哪儿铺开。前两年,一个朋友辞了份稳稳当当的工作,跑去城边开了家小小的旧书店。刚开始,旁人眼里的不解和担忧,像小刺儿似的扎人。他倒好,一头扎进那些旧书堆里,每日掸灰,理书,脚步轻快,像是踩着自个儿心里哼的小曲儿。有一回我去看他,他正捧着一本旧日诗集,书页里夹着一片干透的紫藤花瓣,薄薄的,像褪了色的蝴蝶翅膀。“你听,”他忽然侧过头,笑着对我说,“这地板吱吱呀呀的,是不是像在讲古老的故事?”他脚下的路,是自己选的。在这路上一走,连那些沉睡多年的书页,也仿佛被惊醒了,重新吞吐着光阴的气息。
眼神和脚步啊,常常是分不开的。想起乡下的堂伯,守着几亩水田过了一辈子。他总爱弓着腰,细细查看稻穗的长势。那眼神,温和又专注,像是在看自已亲手拉扯大的孩子。田埂上,他来回地走,脚步踩在泥土里,稳稳的,笃笃的,像是给大地打着拍子。
稻谷熟了,金灿灿的浪头一直涌到天边。堂伯站在田头,身影小小的,可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和他脚下的路,早就长成一体了。那目光是鼓槌,脚步是鼓点,敲着一支只有土地才懂的歌谣。车辆又进站了。身边一个小伙子,脚步忽然顿住。他直愣愣地盯着站台外头那棵玉兰树。风过,几片花瓣悠悠地飘进来,打着旋儿,在灯光里轻轻落下,像几片打着哈欠的白色小羽毛。他慢慢蹲下身,掏出手机,镜头对着落在水泥地上的一片花瓣。他停住了脚步,目光留在了这片小小的洁白上。就这一瞬间,硬邦邦的站台,好像也跟着软和了,晕开一小片被我们匆忙脚步踩丢了的春意。
生活这团泥啊,生来是没个定形的。捏出什么模样,靠的是我们投向远方的眼神,和脚下迈出去的步子。目光是点染它的釉水,脚步是煅烧它的窑火。
当一片小小的花瓣,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落在你的鞋尖上,整个秋日,好像就在那一刻,轻轻地、轻轻地,对你敞开了心门。生活的模样,原就是我们目光点染的釉色,加上脚步煅烧出的窑变,在长长的时光里,一笔一笔,慢慢描画出来的。它不事声张,却自有种朴素的光芒,安静地亮着。
编辑:梁鹤龄 胡丽丽 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