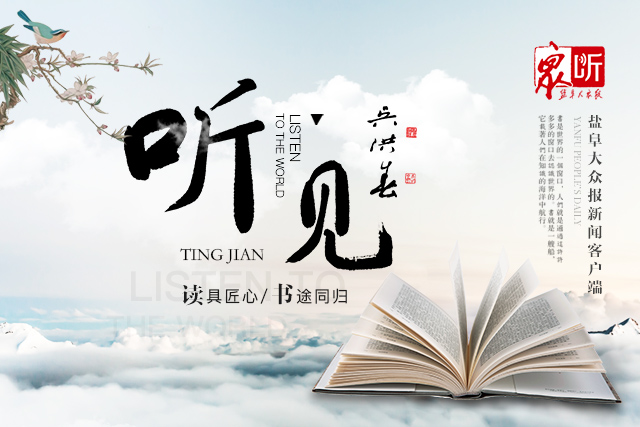
童谣
●颜良成/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盛世修志。近年来,各地都在兴修志书,我也有幸参与乡镇志的编纂。一夜之间,那些尘封的往事成了稀罕之宝。一日翻阅书稿,一首童谣《摇摇船》映入眼帘:“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对我笑,夸我好宝宝.”古老的童谣,仿佛一股清泉,流入心际,亲切又遥远,熟悉又陌生。它像日月星辰,照亮遥远的童年;它像盈盈风铃,叩开美妙记忆的闸门。久违了,古老的童谣。
据考证,童谣最早始于《诗经•国风》:“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在那些风轻云淡、草青柳长的岁月,总有一群穿着开裆裤,甚至光屁股的孩童,手拿篾片木棍,跳跃在村头巷尾,用稚嫩的童音吟唱属于自己的歌谣。我的童年是在奶奶和外婆的童谣吟唱中度过的。那时的老人们一手臂弯里抱着娃儿,一手轻拍娃儿的后背,有节奏地唱着:“宝宝乖,吃鱼腮;宝宝痛,吃鱼冻。”一般人家有五六个小孩,年长的哥哥姐姐将从长辈那里学到的童谣,咿咿呀呀地教给弟弟妹妹们。每到夏日的傍晚,人们便围聚在广场上,由祖母或母亲领唱,孩子们一条腔地跟着唱,边唱边表演。
还有通过简单的歌词,教授牙牙学语的稚童数数,《打老虎》:“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见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一二三四五。”《数青蛙》:“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以此类推,未进校门的孩童便学会了乘法。更有通过吟唱童谣,教育孩子学习知识:“牵牛花,爬高楼;高楼高,爬树梢;树梢长,爬东墙;东墙滑,爬篱笆;篱笆细,不敢爬,坐在地上吹喇叭…”孩子们又唱又跳,乐此不疲。
有一种无厘头童谣,说不出什么意思,但朗朗上口,好唱好记又好玩,大人小孩拍着手齐声唱和。老槐树下歌声笑声响成一片,荡漾在夜空。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颠倒歌,趣味横生。“东西路,南北走,顶头碰上人咬狗。拾起狗来砸砖头,又被砖头咬了手。老鼠叼着狸猫跑,口袋驮着驴子走……”“太阳出西落在东,胡萝卜发芽长根葱。天上无云下大雨,树梢不动刮狂风,纸糊的灯笼刮不动,碓臼刮到半空中.”我们还夹杂着自己幼年的想象,自编颠倒歌词,嬉戏逗唱,乐趣无穷。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知从何时起,那些口耳相传的童谣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终于在历史长河中沉寂。现在幼儿园里也教童谣,老师教一句,孩子们学一句,整齐划一,却总让人觉得少了些什么。我想,少的或许是那种口耳相传的温热,是祖母搂着孙儿时,从皱纹里溢出来的那份情意罢了。
那些曾在一代代人口中流转的童谣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心中不免有些空落和惆怅。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人们会从我们编写的乡镇志中发现这些童谣。虽然是一鳞半爪,但总是历史留存的音符,总有研究的价值。于是,我想在乡镇志中加大童谣的分量,可是,写着写着,却发现记忆已经模糊了。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词句,像退潮时的贝壳,不知不觉被时间的海浪卷走了许多。再有一二十年,恐怕在历史的海滩上,很难找到一些古老童谣的痕迹了。
编辑:梁鹤龄 胡丽丽 马语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