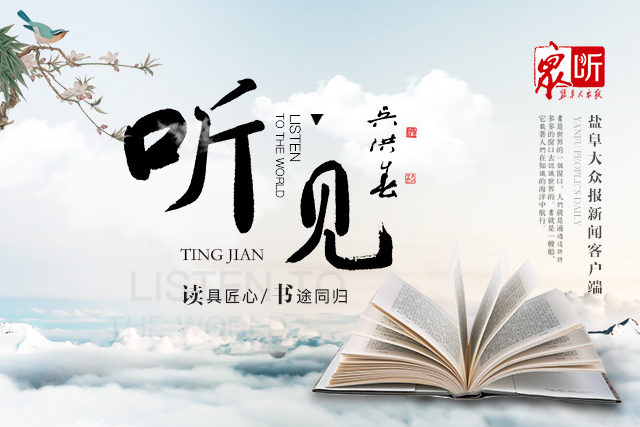
小区面馆
●曾从善/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凌晨三四点,天还没亮透,老家的鱼汤面馆里就飘出阵阵香气。盐城人吃面讲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这清汤底里藏着真功夫——鲫鱼脊骨剁成寸段,文火慢煨数个小时,直到汤稠浓白,铁勺在汤锅里划出金黄的圆弧,乳白的鱼汤便漫过碗沿口,凝成琥珀冻一般。
煮鱼汤是细活,更是慢活,时间,火候,快不得也急不得,稍有差池,味道便天差地别。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随着父母和姐姐离开了拥挤漏雨的学校宿舍,搬进五星小区。小区西南角落,有一家小面馆,没有阔气的门面,甚至没有招牌,只有老板手写的挂在门口的“老上海鱼汤面”这几个字。老板煮面,老板娘盛汤,面在沸水里翻几个滚,雪浪似的冲进碗里,火候时间控制得刚刚好,鲜得人直咂嘴。那时工资不高,面也不贵,两三块钱一碗的面,配上不要钱的咸菜酱土豆,一家四口三碗面,暖胃、暖心、暖了无数个清冷的冬日。
老板是上海人,腼腆不善交流,从只言片语中得知是上海来的下乡知青,在盐城扎了根。老板娘是地地道道的盐城本地人,热情好客,能说会道,时不时和食客们打趣。从早上六点到十点,面馆的人进进出出,周围摊贩、社区的食客慕名而来,老板娘便拿着汤勺来来回回吆喝“给您加的汤来喽”。老板娘把这一勺勺汤当成“宝贝”,面对吃不完的食客还会在收拾的时候小声抱怨“我这熬了几个小时的汤都浪费了”。热腾腾的气息萦绕在面馆里,每天早上的鱼汤面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爸爸总是早早地起床,叫醒熟睡的我们,“面馆开门了,趁早上汤鲜去吃面,后半茬汤淡了。”
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年纪大了,儿子儿媳有时在店里帮忙,但面馆还是时不时休息歇业。再后来,老板一家搬去了上海。面馆最后开业的那天,老板请大家免费吃了一次面,老板娘开心地炫耀儿子给买的首饰,夸赞儿子儿媳有出息,老食客们也真心地祝福。
但似乎大家对这不足十平方米的小面馆充满不舍。
现在,盐城的大街小巷街口路边的面摊小馆渐渐消失在城市发展的洪流中,再找不回以前那“热腾腾的气息”了。再有一年,离开盐城就整整十年了。从校园走上工作岗位,兜兜转转换了几个地方。每次回家,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鱼汤一口面的滋味,坐下来,慢下来,夹一小勺咸菜放在汤勺里,夹一筷子面慢慢盘旋放入口中,迅速把咸菜随着面含住,再舀一勺汤,这就是世间最美味的味道。
编辑:梁鹤龄 崔治国 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