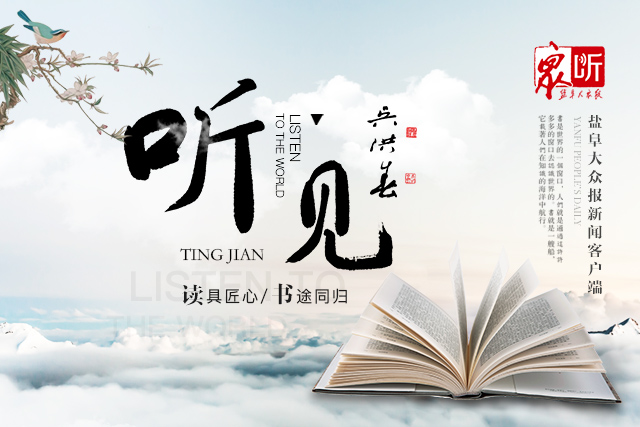
童年
●韦江荷/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记得年少时。家乡是清一色的土坯茅草房,又矮又小,即使这样一家十口人照样住。一张床上你挤我我挤你,铺一层干稻草再铺一条破棉絮倒也睡得温暖而香甜。
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排平房,是建给从城里来的人家住的,不大,一家差不多两间,唯一比我们好的它是砖墙而已。
记得有一年我过生日,母亲向六婶借鸡蛋,母亲站在我家墙的这一边,扯着嗓门就喊:“六婶,我家二子今天过生日,跟你借两个鸡蛋啊!”没过多久,六婶就从墙那边探出头来:“二子是我侄子,我送两个鸡蛋给孩子吃,不用还了。”那时乡风很淳朴:小孩生日吃一只鸡蛋,大人生日吃一碗面条。那年我10岁,吃了煮鸡蛋,也吃了煮面条,双份的喜悦让我喜不自禁。
去年,有位苏州同学毛毛要到我的小城看我。在饭桌上谈到了我们小学时的许多趣事,她甚至还提到有一次我上学没穿裤子,老师不让我进教室的事。我真的不记得了,而这个情景她却记忆深刻,边说边笑得合不拢嘴。记得父亲有一件毛呢中山装,那可是当时的稀罕物,父亲宝贝着,全家人更宝贝着。这件中山装是舅舅赠送的。父亲除了外出走亲戚才拿出来穿一穿。他不穿不打紧,以致左邻右舍相亲的订婚的结婚的,都向父亲借,父亲总是二话不说,很爽快地借给人家。
一次有个人借去走亲戚送还我家时,衣袋下烧了一个洞。为此,母亲责怪了父亲一顿,接着她靠在罩子灯下,一边流泪一边修补。
我在文学上取得的一些成绩,还真的要感谢那时来自无锡的一户人家。他们有各种书籍,小孩们也都有小人书看。一来二去与那些有书有报的人家混熟了,我就一头扎进去不能自拔。那时看的书籍有《吕梁英雄传》《红岩》等。一些外国书籍里的人物名字很长,我读起来不那么顺畅觉得非常拗口。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刘玲见我聪明,就一次次给我讲解一些人物和故事梗概。儿时的我聪颖也特淘气,接受能力强,没上学前就识得很多字,脑瓜子也挺灵活。因为淘气也没少受皮肉之苦,但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为还是非常有数的。我也遇到过奇葩的事。一次傍晚放学,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堂弟,他背着半蛇皮袋的东西,汗淋淋地跟我说:“二哥,给你两个甜瓜。”说完,他便一溜烟跑了。面对诱人的香味,我禁不住用背心擦拭,还没吃就觉得有一只手朝我后肩轻轻拍过来,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我认得那位老者。
“怪不得我家瓜园的瓜都没了,原来是你偷吃了?不告诉你父母也行,你可不许走,等我来了再走好不好?”他不打骂,又不告诉我父母,这真是求之不得,我头点得像小鸡啄米一样:“我不走,我肯定不走。”结果,他摘来一筐甜瓜叶,笑嘻嘻地让我脱掉衣裤,然后抓起一把甜瓜叶,在我的全身上下反复擦拭,最后皮笑肉不笑地扬长而去⋯•这一招真狠,殊不知那甜瓜叶上布满毛茸茸的刺,那么一擦一揉可了得,细刺钻进稚嫩毛囊,那滋味又痛又痒,越痒越要抓挠,以至抓出血来。
长大后与母亲谈及此事,母亲说:“你当时咋不说?”我说:“怕你打嘛!”母亲忿忿不平:“如当时我知道了非找他不可。怎么说还是不懂事的孩子,有事跟家长说嘛,我会教育!”对于这件永远抹不去的往事,现在想来,老者倒也十分睿智,最起码让我记得,尽管那次“偷瓜”真的不是我所为。
编辑:梁鹤龄 李艳 胥文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