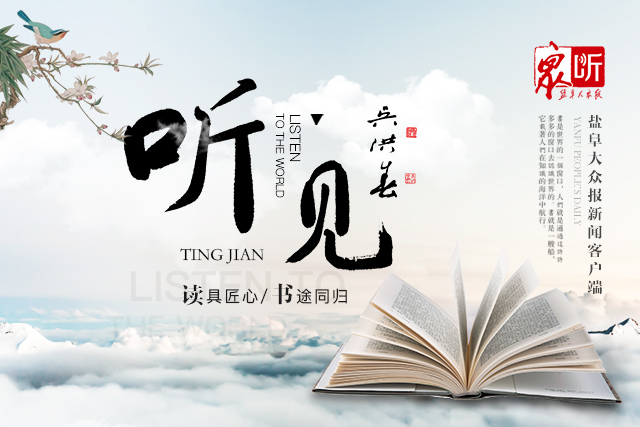
柿果芬芳
●张义奇\文
●凌敏\诵读\音频制作
远在家乡射阳河畔的弟弟寄来30多斤黄澄澄的柿子,还打来电话:“今年虽然经历了高温酷暑,但老家的柿子树却挂满硕果,您要多少我就寄过去多少。”瞅着这饱满而扁圆的半熟柿果,母亲的笑靥迭现于我脑海。我一边翻找旧棉胎、旧棉衣准备“捂”柿子,一边构思着2025年新春联—一把母亲的名字“梅”生动地嵌入其中。
母亲喜好柿树、爱吃柿果。我孩童时就知道屋后池塘边长着两棵柿树,听母亲说那是1965年她出嫁时,从百里外的娘家带来栽种的,经过外公亲手嫁接后终于结果子了。母亲是当地村里第一个种柿子树的,此后她又从娘家陆续引进和种活了李子、枇杷、水瓜、白扁豆等。
记得我上初三那年,当地粮食忒紧缺,左邻右舍开始砍果树,说是果树占了土地、虫害严重,不如长庄稼能填饱肚皮。母亲把自家梨树、李树、枇杷树刨掉了一大半,两棵柿子树则坚决不动。每年摘下的柿果被母亲装篮送给卫生院的尹医生、供销社的龚大姑、电影队的陶队长•他们都是母亲先后做了三次肿瘤手术时忙前忙后的“大恩人”。母亲还把柿果与兴化、赣榆来的渔民交换鱼虾蟹,让祖母和我们兄妹都吃到丰盛的时令海鲜、河鲜。
柿子是我们黄海之滨金秋最甜的地产水果,而且柿树春夏秋三季几乎都是绿叶常驻。春夏之交,柿树开花,在四瓣星状花朵、嫩黄色花蕊之下,我抱着大橘猫去赏花、闻香、逮蜜蜂,猫儿不停地上蹿下跳,在树枝间腾跃追扑。暑假期间,我们兄妹常在柿树下洗衣服、择韭菜、剥玉米,还呼朋唤友一起听收音机里的《岳飞传》等评书。伞形树冠遮蔽了骄阳,徐徐微风泛起池塘涟漪、我们的暑假多了诗情画意。即使寒冬,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我也习惯在柿树下朗读和背书,一会儿手捧课本声情并茂地诵读,一会儿像登台演戏那样,对着蜷伏在树桠间的猫咪自问自答。有一次,居然引起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原来是起早挖田的堂嫂循声而来…
深秋是老少弯腰的丰收时节,母亲忙于摘棉花、收黄豆、晒角干子,中饭做迟了就让我们兄妹三人放学后先吃柿子充饥,香甜、清冽、嫩滑的红柿子让我一嘬就甜到心头。
“秋来柿果满枝头,一半朱红一半羞。”母亲带领我们采摘泛黄的柿子,我一跃爬上柿树,脚踩着树权,用剪刀剪下柿果扔在地上,弟妹争抢着分拣装篮,母亲则不停地指挥我:“摘这个,上边的不动,留给鸟吃。”“沙鸥径去鱼儿饱,野鸟相呼柿子红。”晌午时分,喜鹊成群结队赶来争啄这些“美食”,叽叽喳喳扰了我的午睡,我并不气恼,因为终于领悟到母亲的善心美意。大雪飞扬草木枯,那一个个高悬枝头的红柿子分外耀眼,犹如寒冬挂灯笼,点亮了灰蒙蒙的天空,温暖了我们的身心。两年前我调到南京工作,在第一场瑞雪漫舞的清晨,我一踏进办公区大门,就被办公楼前几株柿树上的红果子吸引住,挺拔于寒风黄叶中的它们如同一盏盏、一簇簇诱人的“红灯笼”,正与隔路相望的“人民电业为人民”七个正红色大字遥相呼应、彼此映衬。
六年前,村里为了土地流转搞平田整地,母亲栽的两株柿树结束了不平凡的使命。此后每到柿果上市,母亲总是为缺了柿树而唉声叹气,护理她的阿姨经常揶揄她:“您就像柿子树倔强固执,像柿子表里如一!”弟弟在四年前带着他的一双儿女到老家自留地栽上了两棵新柿树,还栽了黄桃、葡萄、猕猴桃等果树作伴。柿树开花结果了,可是母亲却因疾病去世了。“百舌鸟啼柿园里,果香扑鼻醉人愁。”现在,老家那片“小果园”无论花儿缤纷,还是树果压枝,永远是我心中最醉人的芬芳。
编辑:张伟伟 李艳 吴玉楼










